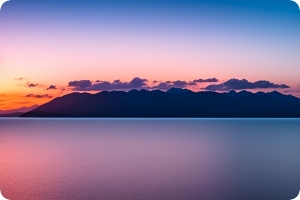谈自杀散文 汪曾祺谈散文
本文目录一览:
- 1、加缪谈自杀
- 2、向死而生散文随笔
- 3、鲁迅《女吊》散文全文
加缪谈自杀
最近总是绕不开这个话题:自杀
刚刚写完《自杀者的天堂》,不到两周,翻开加缪的《西西弗神话》就遭遇了加缪将近八十年前的一篇“荒诞与自杀”。
作为尼采的追随者,“上帝”既然被判处了死刑,用什么其它的价值观念代替上帝呢?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“人”必然面临荒诞感。
虚无主义者加缪在此讨论的是一个作为哲学问题的“自杀”。无论是王小波笔下年代的荒诞感还是个体人生永恒的荒诞,如果人生被定义为荒谬,那么荒诞地存在下去吧!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这不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吗?
摘自:《西西弗神话》 — 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
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便是自杀。 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,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。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,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,全不在话下,都是些儿戏罢了,先得找到答案。如果真的像尼采所要求的那样,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受人尊敬,那就懂得这个答案的重要性,因为接下来就会有无可挽回的行为了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,心灵是很容易感知的,然而必须深入下去,在思想上才能使人看得更清。
倘问凭什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紧要,回答是要看问题所引起的行动。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去死的。伽利略握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,但这个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,他便轻易放弃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他行之有理,但不值得。加上恰如其分的抒情表达,才能既打动我们的感情又照亮我们的思路。对如此朴质如此悲壮的主题,可以设想,精深而古典的辩证法应当让位于比较谦逊的精神气度,既出自人之常情,又富有同情心理。
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。我们则相反,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。 自杀这类举动,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,是在心灵幽处酝酿成熟的 。本人则不知情。某天晚上,他开了枪或投了水。一天我听说,一位房产总监自杀了,因为五年前死了女儿,之后,他变了许多,此事“把他耗尽了”。甭想找到更确切的词了。开始思索,等于开始被耗。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。耗虫长在人心中。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。
这种死亡游戏,从清醒面对生存到逃离光明,我们在某种意义上,像在情节剧里那样,等于自供。就是自供跟不上生活,抑或不理解人生。但也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,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上来吧。那只不过供认“不值得活下去”罢了。生活,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。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,出于多种原因,其中首要的是习惯。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,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,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,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。
究竟哪种不以估量的情感剥夺了精神赖以生存的睡眠呢?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,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。但相反,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,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。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,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希望被剥夺了。
把问题的措辞倒过来, 不管自杀或不自杀,似乎只有两种哲学解决办法,要么是肯定的答案,要么是否定的答案,这未免太轻而易举了吧! 应当重视那些疑团未解的人。窃以为他们属于大多数。我还注意到,一些人嘴上否定,行动起来好像心里又是肯定的。事实上,要是接受尼采的准则,他们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肯定的。相反,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倒确信无疑。这类矛盾经常发生。甚至可以说,在这一点上,相反的逻辑显得可取时,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。把哲学理论与宣扬哲学理论的行为进行比较,未免太俗套了。但应当明确提出,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的思想家中,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、传奇人物佩雷格里诺斯和假设人物儒尔·勒基埃,没有一位将其逻辑推至排斥人生的。据说叔本华面对丰盛的饭局赞扬过自杀,并常拿来作为笑料引用。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。叔氏不把悲剧当回事儿,虽然不怎么严肃,但终究对自杀者作出了判断。
面对上述矛盾和难解,世人对人生可能产生的看法和脱离人生所采取的做法,这两者之间,难道应当认为没有任何关联吗?对此,切勿夸大其词啊!人对生命的依恋,具有某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强的东西。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,而肉体则畏惧毁灭。 我们先有生活的习惯,后有思想的习惯。当我们日复一日跑近死亡,肉体始终行进着,不可折返 。总之,这个矛盾的要义包含在我称之为隐遁的内容中。比帕斯卡尔赋予“转移”一词的内涵,既少点儿什么又多点儿什么。
致命的“隐遁”即为希望是本散论的第三个主题。所谓 希望 ,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,应当“对得起”才行,抑或是自欺欺人: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,而是为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,让理念超越生活,使生活变得崇高,给生活注入意义,任理念背叛生活。
这么说下去大有故意把水搅浑之嫌。至此,玩弄字眼并非枉然,假装相信拒绝人生有某种意义,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活。其实,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任何硬性标准。只不过不要因上述的含糊其辞、离弦走板儿和自相矛盾而迷失方向。应当排除万般,单刀切入真正的问题。 世人自杀,因为人生不值得活,想必是没错的,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,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。这种对人生的大不敬,对投入人生的否认,是否出自人生无谓说呢?
人生之荒诞,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 ?这是在拨冗删繁时所需揭示、探究和阐明的。荒诞是否操纵死亡?必须优先考虑这个问题,甭去管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和无私精神的把戏。在这种探究和激情中,细微差别呀,各类矛盾哪,“客观的”智者随时善于引入各种问题的心理学呀,都不重要了。只需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维,即逻辑。不容易呀。有逻辑性倒不难,而自始至终合乎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亲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这般沿着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。于是在思考自杀时,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: 是否存在一种直通死亡的逻辑? 我在此指明了推理的根源,只有不带过度的激情,光凭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进行推理,我才能知道这种逻辑。所以我管这种推理叫荒诞推理。许多人已经着手进行了。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锲而不舍。
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揭示世界统一体不可构成时惊呼:“这种限制性把我引向自我,在自我中,我不再躲到我一心表现的客观论点背后,无论是我自身还是他人的存在,对我都不再可能成为对象了。”在许多人之后,他又使人想起那人迹罕至、无水缺源的境地,在那里思想达到了极限。在许多人之后,大概是的吧,但那些人又是多么急于求成啊!许多人,甚至最卑微的,都到达了思想动摇的最后转折点。这些人在到达转折点时,纷纷摒弃了他们一向最为珍视的生命。
另一些人,即思想精英们,也摒弃了他们的生命,但,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,是在精神自杀中进行的。真正的拼搏「在于密切注视遥远国度的奇花异木。 对于荒诞、希望和死亡互相纠缠的无情游戏,需要有得天独厚的观察力,即执著力和洞察力 。这种胡缠乱舞既简单初级又难以捉摸,但智者可以解析其图形,而后加以阐明,并身体力行。
向死而生散文随笔
向死而生散文随笔1
古希腊有两个军阀长期争斗,战乱不止,最后一个军阀通过奇袭打败了对手。对手十分勇猛,被羁绊后,仍然大骂对手邪恶,用极其卑劣的手段达到其目的。古希腊对于战争历来有传统,在交战前必须告诉对手自己队伍的人数、装备、交战地点和时间。胜利的军阀一遭对手辱骂,也觉得自己违背了公义,便断了杀他的心,当场解除枷锁,予以释放。
故事见于《蒙田随笔集》。蒙田还说起另外一个故事。腓尼基国王长期追杀一个士兵,士兵流窜多年终于被捕,押入王宫时,士兵也知必死无疑,不免瑟瑟发抖。到了庭前,士兵忽觉以这样的面目见国王,会被耻笑,便气定神闲的入内。见了国王,他反而高声挑战,要求与国王进行决斗。国王听罢,不敢应声,继而佩服其勇气,下令赦免他全部罪行。
蒙田说,当遭遇非难时,我们只有两种方法:一是低声下气的求饶。另一种就是不屈以显自己的勇敢。只要对手的心灵没有陷入邪恶的深渊,一般都会欣赏勇敢、气度和正直。这是人性光辉相兼容之处。
动物界也有向死而生的勇气,山羊遭狼群猎杀时,走投无路之下,会突然返身,主动进攻恶狼。野马在猎豹的追赶下无法脱身时,也会集体返身,进攻猎豹。从本质意义上说,动物的向死而生也有英雄主义色彩,是血性的一次喷发。但弱小动物的命运最后以惨败被食告终,因为动物之间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,强者不会欣赏弱者精神层次上的强大。所以蒙田伤感的说,弱者示强的前提是,对手心中必须无邪恶。
向死而生散文随笔2
老母亲前段时间因着一些事得了抑郁症,病情十分严重。我们见她似是换了一个人,原本勤劳的她什么事也不干,家里从未有过的邋遢。那段日子,她做的唯一的`一件事就是坐在椅子上发呆,不到一刻钟就开始打瞌睡。我们要带她去看医生,她却怒了:“医生就坐那儿问两句,管什么用?!”医学上简单的抑郁症她却觉得没救了。我们劝导她,她却把脖子拧过去,不想听不愿听。我们要带她去旅游散心,她却说了一堆活着没意思之类的消极埋怨的话,在她眼里,世间的人都是无情的,世间的事都是阴暗的。那段时间,于她来说是日日活在煎熬之中,唯有一死才得解脱。我们也知她有向死之心,一旦没看见她就开始提心吊胆。虽如此,老母亲最终还是挺了过来。不为别的,只为她心中还有一丝牵挂。用她的话说:“我若走了,你们就无家可归了。”正是因为母爱,她活了下来。
我有一个同学,毕业后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不久就嫁给了爱情,还生了一个漂亮可人的女儿。原本生活幸福、岁月静好,可好日子没过几年,她的丈夫却得了不治之症,这个打击对他们家来说可谓如雷轰顶。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来临各自飞。若是狠狠心,我同学此时大可带着女儿离开,也不至于人财两空。可人的感情有时候脆弱得不堪一击,有时候却坚硬如磐石,灾难验证着他们的情比金坚。虽知徒劳无获,她仍选择了飞蛾扑火,虽知是没救了,她却要与老天拼上一拼,与命运搏上一搏。他们夫妻达成一致,无论如何都要与这病魔来斗一斗,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,变卖了房屋,借尽了亲朋好友,想尽了一切办法。在那段暗无天日又短暂宝贵的时光里,她经历了一次次接到病危通知后的恐惧绝望,他经历了一次次化疗时的生不如死,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。可就是如此,病魔依然没有丝毫退却,命运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分毫,求生依旧不得生。
生命是一切之源,是最为厚重的礼物。有些人遭遇巨大的痛苦依然坚韧地活着,有些人明明生存无望依然紧抓求生的稻草,但有些人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选择结束生命,因为失恋而自杀,因为债务而自杀,因为事业不顺而自杀,比比皆是。不过是在前行的道路上跌了一跤,爬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就是,只要生命还在,人生就有一万种可能,你会遇到更好的伴侣,你会收获鲜花和掌声,你会实现所有的抱负,你甚至会创造世界奇迹。而选择死亡,意味着你亲手铸造了一把锋利的剑刺向最爱你的人,意味着你将变成泥土永远被世界遗忘,意味着你胸中的抱负和对人生的向往从此夭折。死亡就等于结束,结束在痛苦里,结束在怨恨里,结束在嘲讽中,结束在不甘里。而活着就等于希望,等于光明,等于改变,等于创造,等于无尽的可能。
既然不畏死,何不向死而生!
鲁迅《女吊》散文全文
女吊
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:“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,非藏垢纳污之地!”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,我也很喜欢听到,或引用这两句话。但其实,是并不的确的;这地方,无论为哪一样都可以用。
不过一般的绍兴人,并不像上海的“前进作家”那样憎恶报复,却也是事实。单就文艺而言,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,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、更强的鬼魂。这就是“女吊”。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,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,而且随随便便的“无常”,我已经在《朝华夕拾》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,这回就轮到别一种。
“女吊”也许是方言,翻成普通的白话,只好说是“女性的吊死鬼”。其实,在平时,说起“吊死鬼”,就已经含有“女性的”的意思的,因为投缳而死者,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。有一种蜘蛛,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,悬在空中,《尔雅》上已谓之:“蚬,缢女。”可见在周朝或汉朝,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,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“缢夫”或中性的“缢者”。不过一到做“大戏”或“目连戏”的时候,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“女吊”的称呼。也叫作“吊神”。横死的鬼魂而得到“神”的尊号的,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,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。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“女吊”呢?很容易解:因为在戏台上,也要有“男吊”出现了。
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,那时没有达官显宦,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(堂会?)的演剧。凡做戏,总带着一点社戏性,供着神位,是看戏的主体,人们去看,不过叨光。但“大戏”或“目连戏”所邀请的看客,范围可较广了,自然请神,而又请鬼,尤其是横死的怨鬼。所以仪式就更紧张,更严肃。一请怨鬼,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,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。
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。“大戏”和“目连”,虽然同是演给神、人、鬼看的戏文,但两者又很不同。不同之点:一在演员,前者是专门的戏子,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Amateur——农民和工人;一在剧本,前者有许多种,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《目连救母记》。然而开场的“起殇”,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,收场的好人升天,恶人落地狱,是两者都一样的。
当没有开场之前,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,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,就是高长虹之所谓“纸糊的假冠”,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。所以凡内行人,缓缓地吃过夜饭,喝过茶,闲闲而去,只要看挂着的帽子,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。因为这戏开场较早,“起殇”在太阳落尽时候,所以饭后去看,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,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。“起殇”者,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“起丧”,以为就是召鬼,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。《九歌》中的《国殇》云:“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当然连战死者在内。明社垂绝,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,至清被称为叛贼,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。在薄暮中,十几匹马,站在台下了;戏子扮好一个鬼王,蓝面鳞纹,手执钢叉,还得有十几名鬼卒,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。我在十余岁时候,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,爬上台去,说明志愿,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,交付一柄钢叉。待到有十多人了,即一拥上马,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,环绕三匝,下马大叫,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,然后拔叉驰回,上了前台,一同大叫一声,将钢叉一掷,钉在台板上。我们的责任,这就算完结,洗脸下台,可以回家了,但倘被父母所知,往往不免挨一顿竹(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),一以罚其带着鬼气,二以贺其没有跌死,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,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。
这一种仪式,就是说,种种孤魂厉鬼,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,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,但人们用不着担心,他们深知道理,这一夜绝不丝毫作怪。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,徐徐进行,人事之中,夹以出鬼:火烧鬼、淹死鬼、科场鬼(死在考场里的)、虎伤鬼……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,但这种没出息鬼,愿意去扮的并不多,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。一到“跳吊”时分——“跳”是动词,意义和“跳加官”之“跳”同——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,中央的横梁上,原有一团布,也在这时放下,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。看客们都屏着气,台上就闯出一个 *** 衣裤,只有一条犊鼻,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,他就是“男吊”。一登台,径奔悬布,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,也如结网,在这上面钻,挂。他用布吊着各处:腰、胁、胯下、肘弯、腿弯、后项窝……一共七七四十九处。最后才是脖子,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,两手扳着布,将颈子一伸,就跳下,走掉了。这“男吊”最不易跳,演目连戏时,独有这一个角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。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,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,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“男吊”来。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,一手捏诀,一手执鞭,目不转睛地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。倘镜中见有两个,那么,一个就是真鬼了,他得立刻跳出去,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。假鬼一落台,就该跑到河边,洗去粉墨,挤在人丛中看戏,然后慢慢地回家。倘打得慢,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;洗得慢,真鬼也还会认识,跟住他。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,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,或出洋游历一样,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。
这之后,就是“跳女吊”。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;少顷,门幕一掀,她出场了。大红衫子,黑色长背心,长发蓬松,颈挂两条纸锭,垂头,垂手,弯弯曲曲地走一个全台,内行人说:这是走了一个“心”字。为什么要走“心”字呢?我不明白。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。看王充的《论衡》,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,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,却又并无一定颜色,而在戏文里,穿红的则只有这“吊神”。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;因为她投缳之际,准备作厉鬼以复仇,红色较有阳气,易于和生人相接近……绍兴的妇女,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,这才上吊的。自然,自杀是卑怯的行为,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,但那些都是愚妇人,连字也不认识,敢请“前进”的文学家和“战斗”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。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。
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,人这才看清了脸孔:石灰一样白的圆脸,漆黑的浓眉,乌黑的眼眶,猩红的嘴唇。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,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,但在绍兴没有。不是我袒护故乡,我以为还是没有好;那么,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,可以说是更彻底,更可爱。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,使嘴巴成为三角形:这也不是丑模样。假使半夜之后,在薄暗中,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,就是现在的我,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,但自然,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。她两肩微耸,四顾,倾听,似惊,似喜,似怒,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,慢慢地唱道:
奴奴本是杨家女,
呵呀,苦呀,天哪!
下文我不知道了。就是这一句,也还是刚从克士那里听来的。但那大略,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,备受虐待,终于弄到投缳。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,这也是一个女人,在衔冤悲泣,准备自杀。她万分惊喜,要去“讨替代”了,却不料突然跳出“男吊”来,主张应该他去讨。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,女的当然不敌,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,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,就在危急之际出现,一鞭把男吊打死,放女的独去活动了。老年人告诉我说:古时候,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,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,才少有男人上吊;而且古时候,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,都可以吊死的,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,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。中国的鬼有些奇怪,好像是做鬼之后,也还是要死的,那时的名称,绍兴叫作“鬼里鬼”。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,为什么现在“跳吊”,还会引出真的来呢?我不懂这道理,问问老年人,他们也讲说不明白。
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,就是“讨替代”,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;倘不然,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。习俗相沿,虽女吊不免,她有时也单是“讨替代”,忘记了复仇。绍兴煮饭,多用铁锅,烧的是柴或草,烟煤一厚,火力就不灵了,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。但一定是散乱的,凡村姑乡妇,谁也绝不肯省些力,把锅子伏在地面上,团团一刮,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。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,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。散掉烟煤,正是消极的抵制,不过为的是反对“讨替代”,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。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,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,只有明明暗暗,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,这才赠人以“犯而勿校”或“勿念旧恶”的格言,——我到今年,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。
九月十九—二十日